从石峪寺到胶济线:章丘儿女的抗日锋刃 | 山河铭记 烽火留声
新黄河记者:梅寒
新黄河见习记者:夏晰琳
在济南章丘区普集街道三山峪村北的半山腰,一座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石峪寺静卧于长白山下,群山环绕,绿树掩映。这里不仅是古刹,更承载着一段血与火铸就的红色记忆:1938年2月16日,章丘大地上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章丘人民抗日救国军在此庄严宣告成立,点燃了章丘抗日烽火,被后人誉为章丘的井冈山。这支以石峪寺为起点的抗日武装,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成长壮大,其后多数人员汇入八路军主力部队,转战四方,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继续英勇奋斗。他们的伟大抗战精神,永远铭刻在章丘的历史丰碑上,至今仍在石峪寺的斑驳墙壁和展览馆的展陈中静静诉说,激励着后人。
如今,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但精神的火炬从未熄灭。这座纪念馆所承载的,不仅是往昔的峥嵘岁月,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记忆接力。从文化站长王红梅四处奔波、挖掘史料,让尘封的故事重见天日;到抗日后代捐献出浸染血泪的遗物,将家族的悲痛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再到亲历者后裔崔昌俊老人那低沉而真切的讲述,将扫荡之日的恐惧与求生细节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正是这一代代人的坚守与传承,让沉默的石头开口说话,让抽象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最终汇成了一部永不落幕的英雄史诗,时刻提醒着人们: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有力的前行。
600余年古寺见证章丘第一支抗日武装
踏进章丘第一支抗日武装旧址展览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石峪寺。石峪寺不足三十平方米,虽经修缮,但是斑驳的墙壁在述说着它的年龄。从早些年村民挖掘的石碑可以推测,石峪寺最迟建于明朝永乐二年,至今已600余年。这座古老的寺庙,也因此成为章丘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抗日的历史见证。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济南及周边地区相继沦陷。章丘同样未能幸免于难,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在普集海套园、白云湖的牛码头、相公庄等地,日寇都曾制造了骇人听闻、罄竹难书的血案。面对山河破碎、家园被毁的惨状,章丘大地悲愤交加,抗日的怒火在民间迅速积聚。
国破山河在,城陷焉安身。中华热血儿,岂惧东洋人!1938年初,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普集籍进步教师李曼村、宋乐生怀揣救国理想,挺身而出。他们在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廖容标、马耀南、姚仲明等同志的支持与指导下,于石峪寺这座僻静的古刹中,秘密联络并集结了70余名爱国志士。他们之中有农民、有学生、有教师,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拿起简陋的武器,宣誓抗日。
1938年2月16日,这支队伍在石峪寺正式宣告成立,最初称为章丘人民抗日救国军。李曼村任队长,宋乐生任指导员,下辖三个排。这支新生的抗日力量不久后即被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改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六支队第二十一中队。
成立后不久,二十一中队便展现了锐利的锋芒。他们充分发挥本土作战的优势,夜袭日寇设在普集的据点,破袭胶济铁路,截断敌人的运输线,伏击小股日伪军,屡建奇功。他们的行动如同插在敌人交通线上的一把尖刀,极大地鼓舞了章丘乃至周边地区人民的抗日斗志,也让日伪政权为之坐立不安。
方寸记事本记录下一位母亲的泣血坚守
如何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街道文化站长王红梅是关键的推动者。
自2019年展览馆筹建伊始,王红梅便奔走于济南、邹平等地,挖掘史料,征集红色文物。展览馆建成后,她不仅培训讲解队伍,更亲自担任志愿讲解员,讲述这片土地上的英雄史诗。她制作的八期红色短视频系列、80余场饱含深情的现场讲解,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王红梅笔下的《方寸大小的记事本》,承载着抗日女杰张延龄(宋乐生之妻)悲壮而坚韧的一生。受丈夫感召,这位普通农家妇女毅然投身抗日洪流。革命让她付出了惨痛代价:亲哥、亲侄相继牺牲;日寇和亲日分子为胁迫其夫,残忍杀害了她年仅2岁的幼子宋小周,又虐待致其9岁长子宋广坦惨死。
1941年,张延龄在记事本上郑重写下同志供给部等字样,光荣入党,并担任长山县抗日交通站负责人。她不识字就从头苦学,将情报缝进孩子脏袖口,将手榴弹藏于送粪驮篓,在刀尖上为革命传递希望。2019年,其子宋广镇将母亲这本浸染血泪与忠诚的记事本捐赠给了展览馆,成为无言却最震撼的教材。
三山峪村八旬老人讲述日军扫荡下幸存者的生死瞬间
那时我还太小,记忆模糊,但后来常听奶奶爷爷提起,鬼子进村时,母亲抱着我,拼了命往山里逃,连哭都不敢让我哭出声,怕引来鬼子……
8月15日,三山峪村86岁的崔昌俊坐在章丘第一支抗日武装旧址展览馆门前,陷入那段回忆。1942年出生的他,生命之初便已烙上战火的印记。那场发生在三山峪村的扫荡,经由祖辈的讲述,成了他此生虽无法亲身触碰却最沉重的记忆。
除此之外,崔昌俊还从自己干爹口中听过更早更详细的关于日军扫荡的故事。
时间倒退至1939年,那是阴历九月十三,天刚蒙蒙亮,村子南头骤然响起的枪声,撕碎了小山村的安宁。
那声音一响,整个村子都炸了锅!崔昌俊转述着干爹陈明烈的回忆。1939年的那个清晨,陈明烈不过十四五岁的少年。他刚从地里回家准备吃早饭,枪声便响起来了。村中男女老少在绝望的呼喊声中四散奔逃。我干爹说,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会提前烙好煎饼,就为了鬼子来的时候能随时抓起来就跑。
少年陈明烈本能地向北山奔去,那里有他参加游击队的哥哥。然而北山方向枪声密集,他被一颗子弹擦脸穿过,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夜里他(陈明烈)冷醒了,抬起头看,鬼子已经不见了……崔昌俊声音低沉地转述着。
他命大,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又一点点从山上爬下来。崔昌俊说,那一枪贴着脑袋打过去,只是打伤了脸,要是打穿了脑袋,早没命了。
当昔日摊煎饼的炊烟早已飘散在和平的风里,崔昌俊布满皱纹的手掌却依旧紧握着那段未被风化的历史。
摄影:梅寒 摄像:梁明星 剪辑:梁明星 编辑:柏凌君 校对:杨荷放
作者:访客本文地址:https://www.lrpm.cn/?id=19043发布于 2025-08-22 15:09:19
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青团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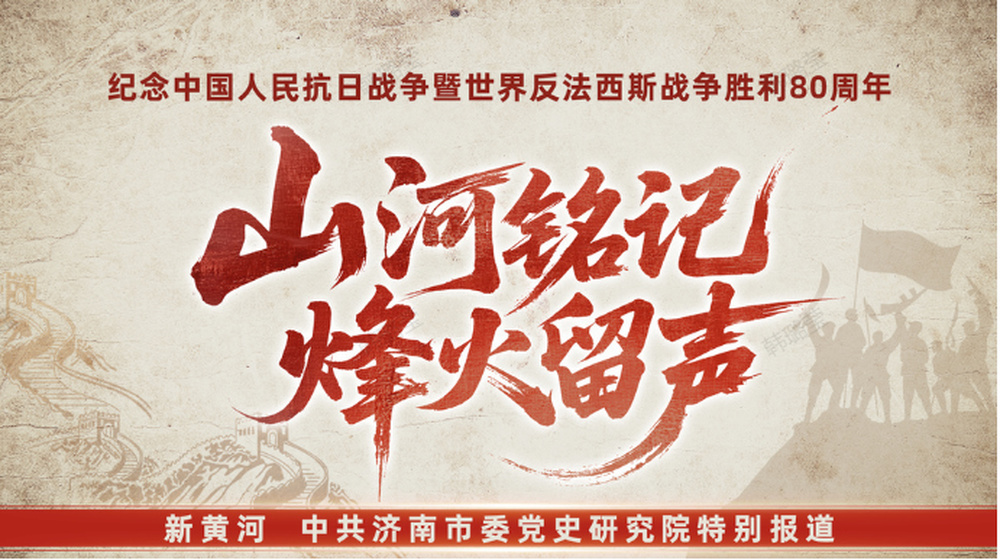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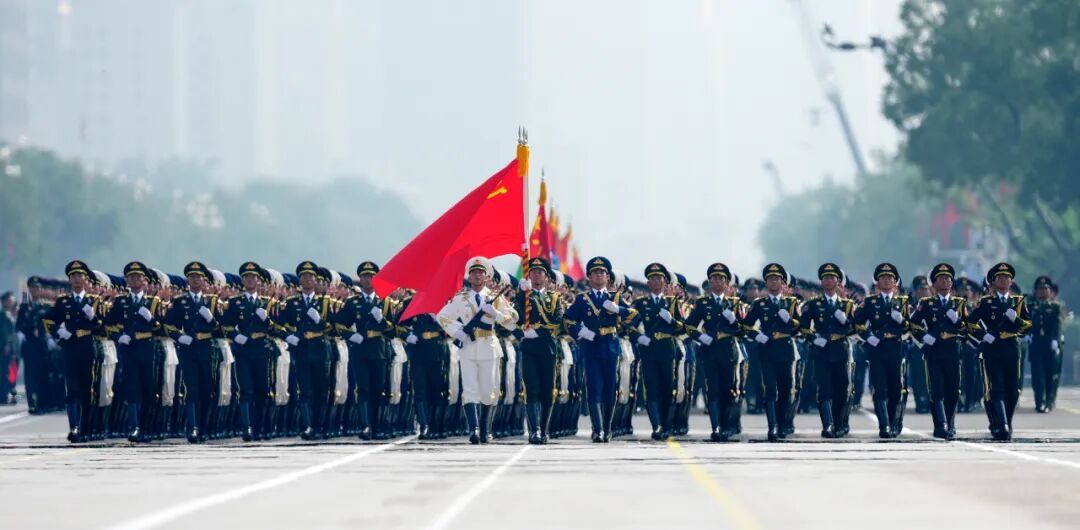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